山本 为秦岭立传
贾平凹第16部长篇小说出版
作者:刘依佳
新闻 时间:2018年04月20日 来源:半岛都市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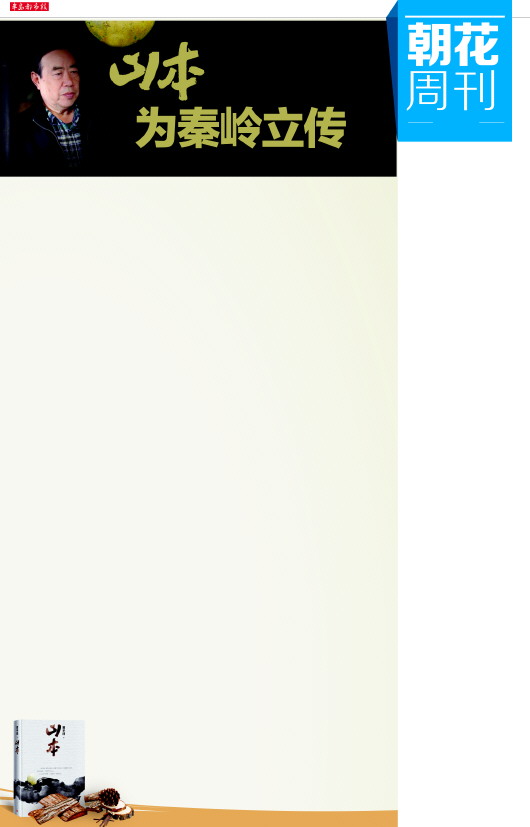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依佳
在一次接受半岛记者采访时,著名书评人绿茶曾说过,作为笔耕不辍的当代文学大家,贾平凹始终深植于生他养他的土壤,他的创作灵感、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与地处秦岭腹地的商山洛水紧密关联着——正如贾平凹本人所言:“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
而今,贾平凹的第16部长篇小说《山本》正式出版,故事发生的地点仍在秦岭。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作者不再把目光聚集到秦岭的某一个点,而是放眼整条山脉,通过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腹地涡镇,一支地方武装从兴起到灭亡的全过程,推演了一部宏阔浓烈又深情悠远的秦岭志,也是贾平凹从“一堆历史中翻出的另一个历史”。
《山本》,一本残酷的书
“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志。” ——贾平凹
初闻“山本”这个书名,记者还真有点摸不着头脑,原来这是一本写山的书。诚如贾平凹所言:“山本,山的本来。”
这山,就是秦岭,一条被尊为“华夏文明龙脉”、在中国地理和历史上都具有至关重要地位的山脉。它横亘南北,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在贾平凹看来,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山本,从字面意思上来说,是以秦岭为本。这本书,也是为秦岭作传的一部书。”《山本》精装版责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孔令燕告诉记者,在贾平凹看来,秦岭是浩大的、宏阔的,可以包含一切,也可以容纳、消解各种人生和时代,“甚至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也是发源于秦岭。但在上下五千年中,人间世世代代,草木生生死死,新旧更替,不着痕迹。但唯一不变的,还是秦岭,它仍旧这么强大、这么稳固地盘踞着。正如贾平凹在本书后记中写道:‘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隅或河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不禁感慨万千。’”
这“爱的花朵”中最浓艳的一枝,便是《山本》的男女主人公井宗秀和陆菊人。用贾平凹的话来说:“那是陆菊人和井宗秀的挣扎、折腾,相互扶持和寄托,演义着他们的一种爱。”
陆菊人生在秦岭腹地纸坊沟里的一户贫穷人家里。她8岁那年,母亲在割毛竹时被葫芦豹蜂蛰死,为了一副入葬的棺材,父亲把她抵给附近涡镇上的杨记寿材家里当童养媳。陆菊人纵然百般不愿,但还是拗不过命运,12岁那年,带着三分胭脂地的陪嫁,嫁到了杨家。也许是阴差阳错,也许是冥冥之中,这块承载着陆菊人隐秘宏愿的方寸之地,竟成为涡镇枭雄井宗秀父亲的墓地。墓地下面,井宗秀还挖出了众多古董和一面铜镜……发生在胭脂地上的这件偶然事件像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钥匙,在亘古不变的秦岭深处开启了一场命运与人性交织、苦难与超脱并存的历史大戏:井宗秀在神秘命运和微妙情感的推动下,成为陆菊人远大抱负的执行者,他从一个资质平平的画师,借助卖古董的钱,通过组建地方武装,与活跃在秦岭中的其他力量相互制衡和争夺,逐渐成为盘踞涡镇的实力霸主,却又在他势力扩张、欲望膨胀的最高峰,突然毙命……故事的最后,在一颗接一颗投到涡镇的炮弹中,所有的热闹全都归于沉寂。只有那秦岭,那屋院之后、城墙之后的层峦叠嶂,保持着永远不变的姿态,一尽着黛青。
可以说,《山本》是贾平凹写得最残酷的一本书。小说写了1927年红军草创时期阮天保与井宗秀分裂的史实。在这场发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纷繁迷乱的历史大戏里,无数无辜的人死于非命。怎么个死法,作家甚至也在书中一一记述。对此,贾平凹表示,井宗秀和陆菊人的土地上长出的这枝花,或许是恶之花,“要写出这种恶之花,必然就得写出土地的藏污纳垢,写出他们身上的毒素和一步步排遣这种毒素。在那个环境里,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人命如草芥,死亡司空见惯。当我写的时候,也是一种恶心、一种悲凉、一种哀叹,所以我写的那首诗最后两句是‘世界荒唐过,飘零只有爱’。”当然,在这个浓稠苦难的人间尘世中,作家也凸显了陆菊人的善良、盲人郎中陈先生的通达、宽展师父的慈悲,这些善意与超脱,是永恒不变、山人的脊梁,也为作品增添了人道主义底色。
一本秦岭版的《山海经》
“随便进入秦岭走走,或深或浅,永远会惊喜从未见过的云、草木和动物,仍然能看到像《山海经》一样,一些兽长着似乎是人的某一部位,而不同于《山海经》的,也能看到一些人还长着似乎是兽的某一部位。这些我都写进了《山本》。” ——贾平凹
贾平凹的小说,向来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土”,方言俚语,世俗风情,都在他的笔端尽情绽放,轰轰烈烈;二是“玄”,那些闻所未闻的飞禽走兽、草木江湖,也于他的描写中活灵活现。具体到《山本》一书,前一个特点有所“收敛”。贾平凹在采访中也称,他此次在写作中注意了对地方特色元素的把握和对语言的运动技巧,希望能做到让其他地方的读者也“能读懂”“能理解”。在阅读本书时,记者能明显地感受到,作者有意在“稀释”语言中的地方特色。
但降低“浓度”,并不等于“改头换面”。字里行间,仍能嗅出商洛特有的味道,仍能随处可见贾平凹炉火纯青的功底。比如在写陆菊人与井宗秀的第一次相遇,作者从井宗秀的角度写道:“这是镇上谁家的女人呢?井宗秀刚有了这般思忖,古柏的柏籽像细雨一样撒下来,在身前身后的地上跳跃不已。”春心荡漾的气息,瞬间见字如面。恰如孔令燕所言:“从开始创作到现在,贾平凹对语言的运用一直是十分讲究的。但他的这种讲究,不是精雕细琢,或是使用很多华丽的辞藻的‘讲究’,而是炉火纯青、自然朴素的一种表达,使他所描写的生活、人物都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在里面。”
而“玄”,则在《山本》里尽情张扬,有过之无不及。那么多暗藏山间、闻所未闻、甚至连名字都不会念的“云、草木和动物”,如《山海经》一般,让读者眼花缭乱,拍案惊奇——
涡镇是秦岭里最大的镇子,从秦岭深山里择川道流下来的黑河和白河滋润了这个有着三万人居住的镇子。白河里有涌泉,涨水的时候看不见,等水流小了,就能看到河心里有一处往上冒泡,像是一簇冲不走的白牡丹,不停地在那里开放。
但有时候,这气泡也不一定是白牡丹,一朵一朵的像是在长蘑菇,这就是斗鱼在作怪了。黑河白河里都有斗鱼,但平日里并不多见。陆菊人有一次去河边洗衣服,就看到了两条斗鱼在打架。它们全身都长得色彩斑斓,“先是眼对着眼,一动不动,再是咬起来了,嘴咬嘴,不松口,后来双方竟绕着如同水中有个轴而旋转,就像是推石磨”。
天晚了,月光下,河边的柳树梢上则会出现一种神奇的鸟,它的头和脸像猫,黄色的羽毛上有黑色的斑点,叫的时候耸着双耳。它一叫,远处的石堤上还有了一只同样的鸟也在叫,声音沙哑,开始似乎在呼,后来又似乎在笑,外人都不认识这种鸟,涡镇的人却认识,说:这是鸱鸺。
还有宽展师父吹奏的尺八,画师修画的特殊技艺,井宗秀制作酱笋的步骤,以及在不同人的眼中不停变化的云……仿似一幅秦岭博物风情画,在作家的笔下尽情地铺陈,“一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而这些“飞禽奔兽、魍魉魑魅”,在贾平凹看来,其寿命要比《山本》里各路贤愚的性命要长得多,“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当这一切成为历史,灿烂早已萧瑟,躁动归于沉寂,回头看去,真是倪云林所说:生死穷达之境,利衰毁誉之场,自其拘者观之,盖有不胜悲者;自其达者观之,殆不值一笑也”。
都说“人非草木”,到头来“人皆草木”;乱世之中,一方水土,生生不息。这,也是来自秦岭的自然、人事和言说的关系,也是作家写作《山本》的初心:“为秦岭写些东西是我一直的欲望,初时兴趣于秦岭的植物和动物,后来改变写作内容的是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里那些各等人物的故事所诱惑。写人更有意义,更能表达我所要写的对于现实的恐惧和对于生命的无奈。”
从2011年的《古炉》,到2013年的《带灯》、2014年的《老生》、2016年的《极花》,此次再推《山本》精装版,孔令燕告诉记者,这是贾平凹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5次合作。“以前跟贾平凹老师聊天,他也经常说起自己的创作思路和创作轨迹。虽然从读者角度来看,贾平凹老师是每隔一两年出一本书。其实他对不同作品的构思,是纠缠在一起的。”孔令燕告诉记者,《山本》是贾平凹2015年开始构思的,在此之前,他刚刚出版了《老生》,2016年又出版了《极花》,期间又发表了很多散文、短篇小说,“所以说,对于秦岭,贾平凹从来没停止思考,也是在思考中,他又酝酿出这样一部大书,一部生命之书、苦难之书,更是一部悲悯之书,一部为中国人写传、为中国人勾勒记忆的大书。”

